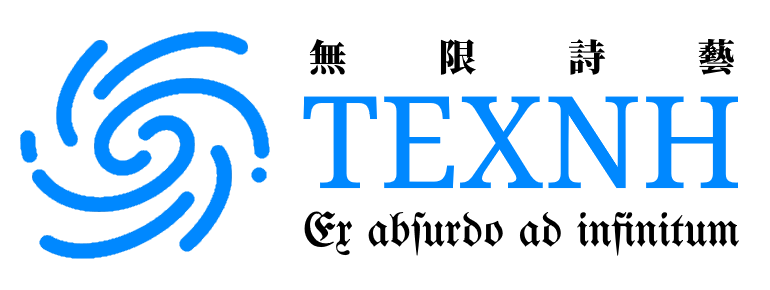鄙人去年读完此书(英文版)后,对其中所描绘世界之景(zhen)象(li)推崇备至,以为不愧为最佳日本科幻。然而此书竟无中文版,甚是可惜,于是暑假自不量力,扬言要翻译此书把握时机好好捞一把。无奈高三忙碌,一拖再拖。本料想反正此书大约四十年来无人翻译,不差我半年拖欠,待我明年再译照样前无古人。于是乎翻译工作自今年二月方始。不料,中途突然发现网上竟有人不到半年全部译出公之于贴吧,颇有不战而败之感,从此一蹶不振。如今见项目重启无望,将全部内容曝尸于此,博君一笑。鄙人从前只参与过用户界面之翻译,经验不足,外加英语水平只勉强够用,文笔亦是糟糕,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拾遗补注:项目文件目前不提供。
版权问题请自重。
以下为不足三章的尝试:
toc.jpg
moon0 序章
moon1 第一章 影戏之海
moon2 第二章 山铜
moon3 第三章 弥勒
moon4 第四章 耶路撒冷
moon5 第五章 失落之城
moon6 第六章 新银河纪元
moon7 第七章 最后的人类
moon8 第八章 长路
moona 后记
押井守的评论
prologue.jpg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几亿年来,波涛翻涌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回响不息,直抵永恒。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它一刻不停地穿行于这个蔚蓝的世界,时而轻柔,时而暴烈,狂野如破晓,平静如深夜。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大海翻涌着。千亿颗闪烁的星星从浪间升起,又在黄昏的暮色中沉入波涛的浩渺。
一天夜里,异乎寻常的黑暗中,一颗微暗的流星割裂了虚空,拖着长长的光尾,坠下焕发着珍珠般光泽的地平线,它的光芒成为了一道永不褪去的疤痕,成为了镌刻于星际空间的记忆。
渐渐地,斗转星移。白星代之以蓝星,橙星代之以红星,它们悄悄逝去,让位于各自的后继者,在天空中编织起新的图案。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时间不慌不忙,泛流过翻涌不息的波涛,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moon0.jpg
时间的洪流在一切事物上毫无例外地留下印记。它在万物中运动,无情地触碰它们、改变它们,更有时毁灭它们。即便是大海也不能幸免。千亿个昼夜里,照耀着大海的星光,吹打着海面的风雨,加热了海水的烈日,旋舞于冰浪的大雪,一切都被吸收、吞没在一个个微粒中,没有一丝对它们久远历史的暗示。然而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保存在无底的沉淀里。
大海——自身就包含了极其悠久的历史,是不可再现事物的永久记录。
关于风、云、浪,关于白昼、黑夜。
大海一直都是时间最亲密的知己。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千亿个昼夜翻涌着。波涛也翻涌着,运动不息。
moon0.jpg
有这波涛之前还有一段时光。在那遥远的日子里,不断积累的高温充斥着这颗行星,地下熔化的岩石和金属喷射着狂烈能量,氢气和氧气在炽热的气体云中旋转,预备着合成为一种新物质。巨大星球的表面密布沟壑,爆炸性气体和岩浆如巨浪般喷涌上天,扭曲缠绕,然后泼洒四周。原始的山丘拔地而起,然后再次沉入岩浆之中。成片的火焰犹如瀑布,遍布大半个行星。
橙色的恒星统治着整个恒星系,不断迸发的强大磁场直达每一个角落,精确地操控着辐射和热量,触发着这个行星从内到外每一个微小的物理化学变化。
二十亿年辛劳的成果即将显现出来。
厚厚的云层遮天蔽日,阳光照射不到被烈火蹂躏着的地面。穿过灰影,熔岩湍急地冲下,与其他的熔岩流相撞,迸发出万千星火起落,犹如一片沸腾的海洋。爆炸发出骇人的光,照亮了云层下端,炽热的熔渣像是能将诞生它的行星整个毁灭。
厚厚的云层中雷电爆闪,时而将电光投向云层上端。流星雨一次又一次地刺破怒旋着的大气层。落下许多碎片,直击下方灼热的泥地。灭世的大火照亮厚厚的黑暗云层,与随之而来的风暴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得惊艳无比,即使没有人目睹这一切。
造物的盛会就要有了成果。下一幕的舞台已经搭好,就在这覆盖了整个行星的火焰之下。
虽然还要过很久很久,真正的主角才会登场。
moon0.jpg
亿万年前,在遥远而微弱的恒星辐射推动下,星际物质的微粒彼此聚集在这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一切就都开始了。一些物体小到只有一亿分之一毫米,轻灵的光线一个小时都不能将它们推很远。但它们确实来了,缓慢而又匀速地,从遥远的真空姗姗而来。一段不可思议的漫长时间后,这些星际物质渐渐地形成了一团漂浮的气体浓云。
这团接近零下160摄氏度的寒云,犹如挂在群星之间的面纱。它获得了能量,成了一团发光的云——发射星云,流射出属于它自己的荣光。光亮的面纱中各种各样的微粒仍然彼此牵引着,强者吞并弱者,形成无数的小物质块。小块旋转着变成大块,大块变成更大的。终于,最大块的物质控制了整个系统的重力场。这个伟大的物质之帝王已经有了生气,以氢核聚变为其力量之源。另一头,较小的物体被那耀眼的核能横扫归位,形成了一个恒星系。
橙色恒星的核心每秒消耗足足5.64亿吨氢,制造5.6亿吨氦。剩下的四百万吨物质则转化成了散布四周的大量能量。
这独一无二的恒星掌控着十颗行星。最近的离它有四千七百万千米,最远的平均有大约六百亿千米。
从星系中心数起的第三颗,其直径为一万两千千米,公转周期为365天。时间的洪流使其物质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的重力场使它紧缩起来,核心温度上升了几千度。放射性粒子衰变释放的热能又为这烈焰助势。两种能量一同作用,融炼着正在构成行星表面的地壳。
当行星开始释放其核心的巨大热能时,转变的过程加速了。喷出的岩浆改变了地表的物质构成,制造的化合物数不胜数。它甚至将更为复杂的化学物质排放到空气中,使其成为大气的一部分。
最后,地幔中喷射出水蒸气来,在厚厚的云层下搅扰着,犹如深红色的镜面泛着地表的红光。
无数年后,水蒸气变成了一团雾降落到地表。此时的地表依然火柱冲天,烈风遍野。白热化的岩浆如火焰河般流动,席卷荒凉的大地。灼热的云不断爆炸,推移着回到空中的雾。然而,水蒸气逐渐凝结成水滴,直到雾气成为了雨,从雷雨云砧落下。至少几千万年后这雨才能落到地面。
moon0.jpg
又过了很久,最初的雨水降落地面,一接触灼热的地壳便立即蒸发了。就在这不过百分之一秒的短暂接触中,它创造了这个行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奠基的事业终将带来地表的第一片积水,开启一项全新的发展进程。
时间缓缓流逝……一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十万年过去了,一千万年过去了……雨变得更猛烈,变得更密集,变成了滂沱大雨。超高温度的蒸气自地面呼啸而上,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云霄,直到足够长的时间后,有足够的降水把燃烧着的岩浆之海冷却到同一个温度。
几万年里,几十万年里,雨不停地下。终于,火海变成了烫热的泥泽,水火在此斗争不息。火成岩漆黑的山脊慢慢地抬升,穿过盘旋飞扬的滚烫蒸气云。
火焰不得不开始撤退。
而水逐渐占领了最低洼处。在最后一团岩浆冷却后,这里的地面便下陷了。
透水的渣石一吸饱水,其中的小孔就将水锁住,筑成了一道防渗水的屏障。
于是水聚集处出现了水池。大雨依旧无情地冲击着大地。无数狭小的海域逐渐汇集成了广阔的汪洋。与此同时,火山暴虐不止。硫磺飞落如雨,乌云蔽天。岩浆成瀑,流入这个世界新造的山谷。地震与滑坡不断,每天都改变着地貌。大雨倾盆瓢泼,似乎要将一切冲回诞生它们的虚空。
接着,当大气中的能量循环减缓到足够慢时,变得细薄的云层中间出现了缝隙,就像被射出的箭刺穿了一样,使第一束太阳的光芒照射在崎岖的大地上。这束光线穿过了既不像云又不像烟的厚厚的气体层,照亮了焦黑火山口的破裂的边缘,隐隐约约显露了其中冒着蒸气的汪洋表面。岩浆沿着斜坡流下,火山则向四面八方散发着暗色的废气。
就在这时,最初的彩虹升起,在破碎的平原上空,照耀在冲刷着大地和灰云的雨幕上。
是夜,星星出现在新开的云隙里。透过大气的湍流,星光暗淡摇曳。这个行星第一次仰望了孕育了它的宇宙。那时也许它听见了一个声音,从远处呼唤它的声音。群星在破碎的大地上投下它们的荣光,诉说着日后的祥和。这个新生的世界的历史才刚刚开始,距离未来的变迁还有漫长的时光。
moon0.jpg
温热的雨水池里充满了富含矿物质的淤泥,形成了一池浓浓的原始汤。水作为强力的溶剂,溶解了大部分从周围流入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物质混合起来,前所未有的事物诞生了。有机物合成了最初的蛋白质。
时间继续行进,步履无声。
天上的降水和地下的涌水汇集在地表的裂隙处,直至覆盖了行星表面的三分之一。起初,陆地和水域还不能区分开来。低洼处聚集的水原地不动,它仅用自身的重量压迫行星的地幔,使地表下陷得更多。在不断扩张的水域四周,火山活动依然剧烈,喷出更多酸性和碱性的物质溶解于水中。
太阳现在已经能穿过云层,将大量的能量投射在不断扩张的水域上。每天都有几次大雨,雨水注入海洋,冲刷陆地,在海洋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混入许多无机物,使一些特定的地区变得更肥沃。
而灰云变得更薄,在几年之内消散了,只留下了明亮的蓝色天穹。堆积如塔的水汽直上海滨的山巅,模糊了群山的轮廓。这些高山组成了大地的脊梁,每天都以几厘米的速度生长。永不停息的地震和滑坡一直印证着这个行星的成长和变化。
大陆浮现,在周围的海洋间进退。原本简单朴素的海岸线变得复杂,到处被切割出海湾。浅滩处,受侵蚀的斜坡在海岸附近回填了大海。
moon0.jpg
这里,柔波下的某处,形成了构成生命的基本材料——硫、磷、钾和钙,氮、二氧化碳和氨,它们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能把这些物质组合成有机基本生命材料的条件是极难满足的。无数次,众多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只能以失败告终。但不管怎样,试验和失败的过程一直继续着,最简单的生命形式终于出现了。它复制自身,新陈代谢。很难说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生命。这样原始的存在实在太简单了,以至于很难定义它们哪些是生命,哪些不是。但是,渐渐地,它们中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一些成为了吞噬者,而另一些成为了被吞噬者——这就是残酷生存斗争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只有最成功的存在能脱颖而出。在这上古时代的浅滩,富含营养的原始汤中产生的,简单的原始的物质,终有一日,必将进化出智慧,足以挑战孕育了它的自然世界。
与此同时,在海中也发生了一些既稳健又激进的变化。分割大陆的狭小海域渐渐消失,一座独一无二的山峰俯视着行星表面。山尖为坚硬如钢的厚厚冰层所包裹,冰川自此而下,屡屡破坏下方的大地。
四大洋决定了行星的气候,将从水中升起的陆地分为四大洲,创造了其各自与众不同的内陆环境。
至此,在这颗年轻的行星上,二十亿年已经过去。下一个二十亿年正快步来临。
无数新的有机体诞生在海中,漂流,游泳,爬行;有的分裂增殖,有的产卵。
三叶虫出现了,遍布各地,占据了全球的浅滩。凭借着厚厚的硬壳和远比同时代其他生物高级的感觉器官,它们统治了早期的生态系统。长久以来,它们在水中的领地内抵御着一切外来入侵。虽然软体动物和棘皮动物也演化出了具有相同复杂度的内部结构,它们身体的防御结构却完全不能适应挑战三叶虫地位的需要。拥有着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三叶虫分化成了大小不同的许多种,小的只有两厘米,大的可有足足两米半,其物种由此繁荣兴旺。
然而,即使常常被三叶虫群骚扰,在海洋的深处,另一种生物正为接手下一个时代而积聚力量。
虽然这些生物刚开始也拥有厚重的壳,但它们一反这个时代的时尚,逐渐抛弃了厚重的硬壳,装甲缩小成为了轻巧的骨板。体外的鳃收至体内,扁平的身体变成了流线型的锥状。小而圆的眼睛演化成了凸透镜,合并在一起的大量附肢变为少许高效的鳍。
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在一百年或一千年内出现的。而是由于在几千万年来非同一般的执着下,这种生物在突变与选择中获得新生。面对三叶虫无止境的攻击,它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时而走向灭绝的边缘。但每过一次,这种鱼就变得更强,更加适应它们的生存环境。对比这种高效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旧时代的进攻武器和防御结构将全然让位。最后,整片广阔的海洋都成为了生命的舞台。海岸浅滩的主人三叶虫,再也抵挡不住入侵者。三叶虫的生存深度有所限制,一旦有鱼把它们连着厚重的硬壳一起推到海底,它们就回不到浅滩了。
一种生物一停止游泳就必定沉下海底,而另一种生物即使放松了鳍也能浮在水中,二者若是在同一片水域战斗,胜负显而易见。
更糟的是,鱼喜食三叶虫卵和幼虫胜于其他任何食物。当然,三叶虫也吃漂浮至海岸的鱼卵和幼鱼。但是当鱼控制了海洋的广阔区域,三叶虫便因为栖息地的限制而感受到更多压力。
在石质海岸与温暖的海湾中,在喧闹的浪花下,在茂密的丛林间,一个接一个,三叶虫慢慢地消失了。
在这颗行星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三叶虫对鱼的统治权力移交更为戏剧性的转变了。
moon0.jpg
终于,鱼将它们的领地扩张到更远。随后的时代将近结束时,它们中的一些离开了退行的海洋,聚集在日明风清处,勇敢地直面陆地和深入内陆的危险。这些无畏的冒险家的两项卓越成就将载入生命的史册。
先是出现了真正的陆生动物。然后不可避免地,终将出现一种能仅凭后腿站立的新物种。同时,永恒运动中的大海鸣响着,记录着关于各式各样生活在其边缘的生物的歌,关于奋斗、盛衰、未实现的梦想和勇气。
斗转星移,默然无声:从鲸鱼到天龙,从天龙到宝瓶,从猎户到项链。许多闪烁的星星爆炸了,在死亡之焰的一瞬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然后从天空中消失,只留下散发着微弱光线的星云。
漫长的岁月逝去,正如它曾经所为,亦如它未来将为。
直至时间的尽头,假如它真有尽头。
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不断翻涌着,滚滚而来,滚滚而去。
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ch1.jpg
旅人跪倒在地:“啊,好渴!”
大海充斥着无数声响。水中,声音传播的速度比在空气中更快,并且水自己也制造各种声音。复杂的洋流,海底的形状,密布的褐藻,这些都可能使声波发生偏转,或聚集,或四散。
水流搅动着气泡,发出的声响在海底的石隙中穿行。同时,还有另一种声音:贝壳的残片叮当作响,随着潮水翻滚,又落入珊瑚丛中。海岸线上,风吹拂着海浪,卷起浪花朵朵,进退沉浮,响声阵阵如远方的雷。海崖高处,碎裂的石块落下,使得海中深沟震动,在水下激起令人不安的涟漪。
另外就是海中无数生物发出的声音了: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双壳贝类吸水时,发出梦游般的纺车声。
喀喀……喀喀喀……喀喀……
——海星为抓附在岩石上,屈伸着褐色的腿。
喀拉……喀拉……喀拉……
——永远吃不饱的甲壳纲动物挥舞着大钳,喋喋不休。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一大群软骨鱼行进着,发出威风的隆隆声。
鱼儿挥动着鳍,在水中有力地前行,制造的漩涡把周围的小生物抛来抛去。当它们游过之后,发出的声响渐行渐远时,海底的软泥上开出了许多小洞,环节动物从中伸出流苏般的鳃,随着水流摇曳着。这时,一个较大的洞中钻出来一个灰白色的头,然而又被周围摇动的海草惊动,退了回去,鳃也收藏了起来。
咻——……
——一束水流从洞中射了出来。
唰——……
——急促的声音就像大雨击打着水面,预示着又一次尝试。一大群小的甲壳纲动物排成网状扫荡而过。声音延绵不绝,直到队伍到达一道海沟,消失在大海深处。
上方,一条大鱼正追赶着什么,它投下的影子也飞速奔驰,在水中画出一道优雅的曲线。
沙沙沙沙
——鱼鳍大力推动着水流,声音传到了海底。
当这个声音也消散了,大海便陷入了沉默。
现在,只有远方的海浪拍打着海岸,声音在海礁间徐徐穿行。
他重新把头伸出洞口,环顾四周。只见褐藻密林的深处有东西在游动。他时而瞥见一条宽阔的尾鳍,时而瞥见一部分背鳍,又有时是有鳞的一面。最终,它靠近了。原来这是一条性情温和的大软骨鱼。
他正好在那大软骨鱼的行进路线上,于是滑出了洞口。他掠过波动起伏的褐藻,沿着一条海礁间狭窄的小径向岸边游去。大鱼见到他似乎吃了一惊,呼呼地拍打着胸鳍转身就逃。一群小鱼也游入海礁之间,飘游犹如风中的落叶,遍布整条水道。一时间,他除了周围小鱼反光的身躯外什么都看不见了。之后他就身处一片开阔的水域,海底远在视线之外。他明白,如果他顺坡而下,就会进入一个危险的深谷,大量河水在此倾泻入海。他知道,深渊里居住着的都是些怪异的鱼,和他平时在领地内见不到的海草。
于是,他猛冲着穿过深谷,迅速到达了对面的海礁。
这时,那深谷中隐藏着的东西勾起了他的兴趣。它位于两座海礁之间,一半埋在淤泥下,显然已经在那里长眠了很久。即使它仅仅是躺在那里,为深红的铁锈所覆盖,被漆黑的褐藻所包裹,每当他经过时,他仍然觉得浑身刺痛,似乎它在警告着什么。
的确,很久以前他就发现了这个奇怪物体。但他一次都没有下潜去看个究竟。有时,其他海中的生物会冒险进入那个深谷去捕捉猎物,却常常没命似的逃回到水浅处,好像是被什么恐怖之物吓破了胆。另外一些也许就只能沉入那深不见底的黑暗深谷,再也不能回来。他旋游着,往水浅处游去。
突然,身旁的海浪疯狂地旋转起来。回头一看,他匆匆瞥见一个穿行如箭的黑色身形。他认出了这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硬骨鱼的轮廓。
他转过身去,紧贴着下方的海草游动,然后猛地向上冲,以便当那条鱼再次接近时他能利用高处的优势。又一次,那鱼向他冲来,他侧身一躲。当它第三次游过来时,他用力撞去,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他敏捷地只把最可口的内脏咬在口中,然后用力推开了还在痛苦中扭动的尸体。两名战士周围的海水都被染红了,道道血迹顺着水流流向远处。一群小鱼已经聚集起来。他很快地吞下了肉,又从背上的孔中喷出了刚刚吞下去的水,把一大堆泡沫投向了这些食腐者们。此地不宜久留。因为更大更凶猛的鱼会循着血的气味而来,任何时候它们都有可能出现在这里。于是他摆脱了跟随着他的那群小鱼,乘着大浪游向海岸。鱼鳍一振,他就到了一片安全的矮礁,这是他喜欢的休息之处。现在,他爬上了一块突起的石头,水从石隙中射出,浪花打在他的后背。
在这个有利位置,他仔细地观望着,一边是铅色的大海,另一边是土黄色的干燥平原。在这里,海洋和陆地几乎是同一高度,只有拍打着冲上海滩一望无际的白色浪带将它们分开。远方吹来的风一刻不停地在他耳中吹着口哨。他想象着这风吹过了海洋,又越过了白浪,拂过平原。他抬高身体,伸长脖子,向平原深处注视着。没有一丝运动的迹象。只有一层土黄色的薄雾轻掩着远方。他的左边,远在地平线处,似有一片树林若隐若现,塔顶一样的尖角从薄雾中显现出来。
这里很安静。非常安静。只有微风的细语和海浪的轻拂。
自从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色,多少个日夜已经逝去?
一种熟悉的不安感又一次油然而生,对这个静止而沉寂的诡异世界,他存有一种本能的怀疑。
风渐渐地越吹越冷,海上的浪也渐渐变大,泼洒着泡沫。
他跳跃着,追赶着风,然后一跃跳回水中,溅起大片水花。他沿着岸边游了一会儿。晶莹的深蓝色皮肤在深色的海浪下时隐时现。他穿行在海礁之间,爬上一块从海浪中突出的平坦石板。石板上,他伸展开疲惫不堪的身体,喷出消化道中的水。一阵大风把水接住,将它拨成一缕水花。他反复几次把头浸入水中,摇动着洗去粘在鳃上的无数沙石。
前方海礁的分布将水路分隔成了复杂的网络。他从未越过现在的位置冒险深入。他总是告诉自己,即便继续向前,所能看到的也不过是同样的铅色大海和薄雾笼罩的土黄色大地。
另外,他也喜欢待在这个突出的石架上。四周的海礁上有许多他喜爱的大个头甲壳纲动物,这干燥平原的景色他一样喜欢。
他用后肢支撑起身体,抬起他又大又圆的眼睛,搜寻着。
后背的孔中喷洒出薄雾,在空中架起一道淡淡的彩虹。
就是这里。
一个巨大的方形出现在远处平原的中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它和任何东西,不论是在这贫瘠的陆地上,还是在这片海景中,都不一样。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是谁将它放置或建造在此。这一真切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是个谜。这个奇异的物体投射出一种不同于此地死寂的感觉,反而给人一种不可接近之感,触摸则是更不可能的了。它触动了他所有恐惧的神经。
而且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来这石架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尽管他对这个物体的本能恐惧丝毫未减,独坐在这广阔虚空中的光景依然使他兴奋不已。
风越吹越大,越吹越冷,吹打着他浸湿的身体。
很长时间,他就这样坐着,面朝平原。
渐渐地,天空和大地昏暗起来,直至分不清它们的界限,直至他能看见的只有那冲上海滩一望无际的白色浪带。不久,黑暗将它也吞没,他对周围事物的知觉仅限于环抱着他的风和拍打着他后背的浪。
他环顾四周,如梦初醒,然后又跳回水中。
随着夜幕的降临,海中所有的生物都从它们的洞中出来,遍布整个海洋。他的前方,有两条大鱼正在格斗。它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像车轮一样旋转着。他靠近一看,只见它们各自咬着彼此的尾巴,事实上,双方鳍后的部分都已经被吞下去了。他继续靠近,抓住它们,又把它们的头分了开来。硕大的脑壳卡住了他的喉咙,但他还是把它们整个咽了下去。食腐者聚集成一群,他一穿过,就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一个明亮的橙色球体正快速接近,现在几乎已经在他的头顶了。强壮灵活的触手猛地伸出,从四处将他的身体包围。这个进攻者他曾在附近见过,是一种多足的软体动物。他挡住了自己的头,刚好躲过了那生物的一咬,然后在水里一踢。他用右肩用力推挤着那软体动物,试着把它抖掉。这通常很有用。但这一次,那东西依然紧抓着他,丝毫没有放松。他转变了策略,向着他头上的坚硬触手咬去,试着把它咬断。这次管用了,其余的触手从后背和两旁被弄了下来后,他就把这袋子似的东西撕成三片,丢在旁边。这个多足软体动物的味道并不坏,对于海底那些流苏状的环节动物来说可以算作是一顿美餐。
他向前加速,经过一段昏暗的水道,来到褐藻林阴影下一片熟悉的海礁。自他遭遇攻击后,鳃的活动第一次舒缓下来。海礁悬空一端的下面有一个小舱,那是他的家。石灰质的贝壳覆盖在上面,顶部裹着宽叶海草,进出的圆形洞口被他磨出了银白色的光泽。如果整个从周围的淤泥中提起,这个小舱可能和上面高耸的海礁一样大,但他对此并不知情。
他从洞口进入,在双壁的茧中安顿好。一堆气泡立即从茧的基底处涌上来,环绕着他的身体。气泡粘上了他深蓝色的皮肤,变成一件镶嵌了珍珠的披风。有东西流进了他的体内。同时,体内累积的东西开始溶解,散流开去。他侧过身来,在茧的底部躺下,入睡了。他不曾去注意卧室底部的气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但它们确实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对他来说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能让他离开这里。
夜晚的海底充斥着各种刺耳的噪音,远处有,近处也有,在他身边混响着,回荡着。他栖居在小舱中,只能隐隐约约感受到环节动物和棘皮动物不停的剧烈活动,和更为简单的生物的运动。他翻了个身,然后进入了更为深沉的梦乡。一条肚子上有着明亮绿色光点的鱼路过这里,一时将嘴拱进了小舱中,却又立刻惊恐地撤了回来,逃入无边的黑暗中。
moon1
又过去了很多年。
每天,他都从自己的藏身处出发,来往于两座海礁之间,去观望那铅色的海洋和土黄色的陆地。除了觅食和睡眠,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里有充足的食物,偶尔与较大的软骨鱼战斗比起任何真正的威胁来更像是一种娱乐和刺激。他从没想过要有个同伴,也没想过能遇到另一个像他一样的生物。
一天,他又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生活:离开藏身处,穿过褐藻林,滑进海礁间的狭窄水道。不知何时,棘皮动物迅速繁殖,覆盖了水道两边的岩壁,以至于看上去更像是海草而不是动物。他注意到,从前成群结队随处可见的半透明的鱼如今却不见踪影。他还发现,其他的小鱼群也不见了,整条水道静得可怕。他推挡着水,放慢速度,环顾四周。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他确信这一点。那些常在海底挖洞并且在水中摇动着鳃的小型环节动物全都躲了起来,用坚硬的头封住洞口。
它们在害怕什么?
他检查了一下海礁,一时神经刺痛,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于是他返回了往常的路线。
当他经过那黑暗的深谷时,他往下一看,发现一群大软骨鱼在谷里偷偷摸摸地游着。
他意识到,它们在下面一定是在躲避着什么。问题是,那究竟是什么?
鱼很少下潜到那里。只能是因为有东西迫使它们到深水处逃生,在更大的危险面前它们忘却了平时的恐惧。
不安的情绪第一次在他心头猛地一击。本能的警觉散发出来,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一时间,他想自己是否应该回到他的藏身处,或者也像这些躲藏着的鱼一样寻求深水的庇护。最终,他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他继续前进,全身紧绷,敏锐地感知着周围海水的情况。
到越过海礁抵达那石架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今天与之前所知漫长岁月中的任何一天都不同。他全身心都被这难以排却的恐惧紧紧地抓住了。探求那恐怖之物的强烈欲望驱使着他,使他登上了那突出的石架。
他的周围是一片铅色的海洋和土黄色的广阔平原。海风从开阔的海面吹来,一如既往地强劲。他冷得浑身发抖。
远处,在平原里,一片浓雾如烟尘一般,摇曳着升上天空。
他的身体僵硬了。
浓雾后的更远处,一个巨大如山的东西正在移动。它的上端直上灰色的天空,形成了至少三个尖顶。他从不知道陆地上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即使是在最晴朗的日子里,他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接着他看到了第二个这样的东西,和第一个一样,远远地在它后面迫近。然后又是一个,从右边滑动到左边,因为实在很远,所以他只在地平线的边缘处辨别出了轮廓。
这些影子般模糊的形象有着奇怪的移动方式,这令他毛骨悚然。
它们会是什么?
当时,假如他曾经见过一座山或仅仅是海下的山脊,他就会意识到他现在所看到的东西与那些巨大的岩石结构有多么相似,这种恐惧就会把他逼疯。幸好,他对山脉或者其他任何这样高大的东西一无所知。这巨大如山之物的移动对他来说则无异于海潮的涨落。
这时,他似乎看见了别的什么,于是伸直身体站到岩石的最高处,那里的视野更好。
在他的左边,远方平原的深处,矗立着一些他总是能在那薄雾中看到的尖角,它们几乎如海市蜃楼一般悬浮于地面上,巨大的尖顶直指那幻境中的树林。
moon1
很长时间,他就这样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真实的幻影。这一刻延续了几个小时,其间,他不断地质问天空和大海,他看见的究竟是什么。
对自己,他也问了一个问题:这儿究竟是哪里?
他能感受到一直紧锁在心的东西铺展开来,在全身散布着一种紧张感。
暴风雨从水面上逼近。倾盆大雨下,他坐了几天几夜。大海无情地在他耳边呼啸着,海浪如震天的瀑布般拍打着他和岩石,弄湿了他的身体。紫色的闪电将浪尖照得蓝白,隆隆的雷声将其振动传播到整片大海。
他在石架上平躺下来,不停地被海浪击打摇动着。
原先海礁边成群的甲壳纲动物和跃动在浪间的银亮的鱼,现在都不见了。即使旁边布满了海底的褐藻林现在也已面无血色——他看到苍白的褐藻一条一条地漂摇着,或是被连根拔起,在永无止息的海浪中旋转。他看到它们在半透明的水面漂流了很久,直到被水流冲回海里。
突然,一阵猛烈的暴风又将他的思绪带回眼前。响亮而刺耳的风声拨动了他的听觉神经,刺激了他,唤醒了他很大一部分至此一直沉睡着的大脑。他抬起身体,向广阔的海洋投去空洞的目光,伫立许久。然后,他整个身体打着冷颤,将自己震入了海浪中。过了一些时间,他才对周围的事物重新恢复了知觉,并且想再看一看平原上那些怪异的巨大形象。
一次又一次,他从浪间浮出,伸长脖子,却只看见陆地上一片空旷。薄雾笼罩的土黄色平原又变得如往常那样,索然无味。
左边,有着尖顶的奇怪树林在远处若隐若现。
这就是全部了。
那是一场梦吗?
他摇摇头。
不安依旧郁积在他记忆的深处。
他径直游过海礁间的水道,快速掠过黑暗的深谷。他看不到哪怕一条鱼,哪怕一小片褐藻。周围只有被贝壳装点着的海礁,和裸露的白沙。清澈的水域如死般寂静。
曾经生长在海底的褐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泥泞的洞中如鲜花般张开它们鳃的活泼生物又怎么样了?
所有的甲壳纲动物和英勇无畏的软骨鱼呢?
阴暗的海底,只有海浪拍打着海岸悠远的低音,和水流摩擦着海礁的高音不停漂流着。
所有那些海洋生物的呼号都不见了。
他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调查起来很危险。他用尽全力游回了他的藏身处,一头冲进洞口。
前所未有的疲惫猛然袭来。他的鳃迅速减缓了活动,他的头往下一沉,陷入了沉睡中。
不久,藏身处括约肌般的入口开始收缩,静静地关闭。一部压缩机工作的微弱声音从下方某处传来。形状尺寸各异的操纵臂从墙上伸出,将银色的针从他深蓝色的皮肤深深扎入。液体流过附在针上的管子,管子开始鼓起。并且越来越多的针管加入了。半球形的帽子盖在他圆圆的头上,成捆的缆线从中延伸出来,如蛛网般布满了整个小舱。然后,两对粗管钻出层层贝壳通向舱外。其中一对开始吸入海水,发出汩汩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另一对开始喷出无数微小的气泡。气泡就像银链一样浮出水面,变换不定的形状给这死气沉沉的荒凉海底带来了一丝生气。
不知不觉地,他睡着了。
ch2.jpg
汝来自尘土,必归于尘土。
这天,塞易斯城依旧炎热,干燥的热风掠过街上的白色鹅卵石不断扑来。松木做的架子支撑着残破的拱门,木头中渗出了红色的树脂,散发出的香气和食盐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一头小驴满载着编织而成的篮子,气喘吁吁,摇头晃脑,艰难地走在石路上。有一只马蝇,长着蓝色的大眼睛,停在汗津津的驴脖子上,像是挂着一块宝石。小驴无人牵引,在街角转了个弯,穿过另一道拱门,走进一条小巷。
这时,小驴的主人在它身后出现了,用力拉住缰绳。
天很热。难以忍受的热。柏拉图抓起他身上的长袍,提高一些,好让微风透进来。他的白色长袍长及脚踝,是阿拉伯人的款式。“那教士的住处离这儿远吗,格拉底乌斯?”
他的随从,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阿拉伯人,这样答道:“老爷,这条小巷走到底有个院子。再过去一点点就是了。”四五年前去罗德岛时,柏拉图雇了这个阿拉伯人当他的仆人。他被邀请去帮助当地的贵族建一个预备学校。那时起,他就非常欣赏他那位同行旅伴广阔的知识面。这一点对于一个社会下层的人来说是很难得的,因此他很快成为了柏拉图最信任的个人助理。
烈日之下,柏拉图眯起眼睛。“但愿已经很近了。”他发了发牢骚,“这位教士德高望重,他拥有的收藏品最好和人们所说的一样。”
“罗德岛的治安官忒律波里乌斯说,他亲眼见过一大堆的书卷。”
柏拉图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
他们经过拱门的阴影,走进一个狭窄的院子。院子里,一棵特别大的柽柳生长着,在不规则的鹅卵石上投下树荫。阳光从树叶间穿过,地上光斑点点,简直就是头顶那圆形天体的无数微缩版本。
“应该就在这里。看,墙上有教士的标志。”
白色石头砌成的矮门边,一块太阳神形状的木头挂在那里,稍微歪斜了一点。堆在入口的篮子都打开着,其中一个装着一个大半空着的袋子,一些谷粒从中洒了出来。
“我去看一下他在不在家。”阿拉伯人说着放下了行李。柏拉图则留在树旁。他的皮凉鞋一路拍打着鹅卵石,直到那座房子。“尊敬的普利可敦大人在吗?我的主人,雅典的柏拉图,在此求见。”格拉底乌斯的声音在院子里回响着。院子四周有一些不太大的屋子,屋子的窗户打开了,人们张望着是谁在说话。见到这个阿拉伯人,或指指点点,或惊声尖叫。他站在那里,身穿暗色麻布短袍、羊皮鞋和铜扣衬衣,额头系着银带,看上去比柏拉图更为高贵。而后面的柏拉图却闲站着,包裹放在脚边,像是被抛弃在院子里。
阴影下教士家门口的芦苇帘被推开,一个老人探出头和阿拉伯人交谈了几句。格拉底乌斯回头,示意让柏拉图跟过来。
居室内部十分简朴,以至于会被错认为是仓库或马厩。二位访客依次通过只有一人宽的石门,进入令人窒息的黑暗中。他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外面的烈日,因此需要花些时间来适应。里面热得可怕。灼热的空气携带着臭味向柏拉图袭来,使他打了个踉跄。阿拉伯人握紧主人的手,扶着他向前蹒跚了几步。
“请在此就座。”
柏拉图正看到柽柳树枝编织而成的坐垫上有个污点,但别无选择,他只好照做。可是为时已晚,他听见了一些私下里针对他的低语。
“……和贤明的梭伦是远亲……雅典高贵的家族……阿里斯通的儿子……柏拉图大师……我的书卷……”
他听到的只是些零零碎碎的词语。他朝着声音来的方向点了几下头,不再试图分辨声音,转而仔细地观察这昏暗的房间。渐渐地,他的眼睛适应了,居室的细节也变得清楚起来。石铺的地面中间安着一个砌成方形的火炉,微弱的火苗在里面闪烁摇曳。火焰上,一个水壶里有什么东西正不停地冒着泡,这就是那恶臭和热气的源头。沿着地面的边缘,各种瓶瓶罐罐随意地排放着。房间一角,被烟灰熏黑了的木质箱子和篮子堆在了倾斜的架子上,摇摇欲坠。
柏拉图发现那低语已经停止。于是他又把注意力转移回那个正蹲下的身影,也就是刚刚叫了他的那个人。
“您就是那位尊敬的普利可敦,亚特兰蒂斯之卷的拥有者?”
这个干瘦的人又低语了几句,轻得连柏拉图都听不见。
“格拉底乌斯,”柏拉图说,“我们的礼物。”他举起一根手指。“不,等等。”柏拉图举起两根手指,摇了几下,以示强调。
“是,老爷。”阿拉伯人点了点头,从包里拿出了两袋金粉递给柏拉图。
“尊敬的大人,这点薄礼请惠存。”柏拉图把这两个虽小却鼓鼓囊囊的袋子放在了那老人膝前的地上。
“礼物!这还真是出人意料。”老人说道,这回他的声音抬高得总算能让人听清了。他向前俯下身,解开系在袋口的绳子,把金粉捏在指间,显然十分满意。
“尊敬的大人,请允许我解释一下登门打扰的原因。”柏拉图开始说。突然,他撇了撇嘴,眉头一皱,把手放进上衣中,努力往背后伸。有活物在那里爬,他能感受到皮肤上的重量,这很不舒服。他用手把它拿下,摔在地上,踩碎在鞋跟下。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教士说。
柏拉图仔细打量着这位尊敬的普利可敦大人。教士中有一些是居支配地位的司祭,还有一些是只在教堂中工作的主持圣餐者。过去,许多主持圣餐者能进而成为大臣或将军,但近年来国王已经大力削减这种事。正因为升官之道被阻碍,两种教士现在都倾向于为发财致富而努力。这尤其体现在,地方特使常常通过购买教士的权威意见来抹消他们的过失,于是财富便饱入教士私囊。
蹲在他面前的老人看上去不像是这种教士。
也许他离开教堂是由于健康问题?
年迈的教士慢慢站起身来,消失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都怪这热气,”柏拉图小声抱怨道,“我在这里没法读东西。”
他推开了坐垫,一屁股直接坐在凉爽的石头上。
过了一会儿,老人又出现了,身后拖着一小捆编织过的细柽柳枝。仔细一看,柏拉图发现这捆成的圆筒中间藏着许多卷布满灰尘的羊皮纸。
“柏拉图大师,这些就是关于亚特兰蒂斯王国的记录。”
哲学家的两眼放着光。他捋起袖子,抽出其中一卷,摊开在地上,全然不顾身旁扬起的灰尘和沙子。但是这里太暗了,什么都看不清。他重新站起来,一把抓起羊皮卷走近房间中央的小火炉。途中,他的脚撞到了什么,发出一声巨响,一些液体溅在地上,到处都是。但他不在意。他把羊皮卷放在火光下,看到上面一行行用伊特鲁里亚语写成的文字。
有名门望族自阿特拉斯而来。钟鸣鼎食,富甲天下,王公贵族,莫能及也。帝国无疆,可使四方之财货贡入。中土肥沃,足令本岛之人民小康。
柏拉图读着,额头上的汗也忘了擦,腿上爬的虫也不顾赶。
海内有矿石名曰山铜,使亚特兰蒂斯万间广厦之四壁皆美于金且坚于铜。
“山铜!”
柏拉图将目光从羊皮纸上抽回,转而投向炉中劈啪作响的微弱火舌。那传说中金属的名字使他想起了关于亚特兰蒂斯这个西方大陆的一些故事,这是他去年在法尤姆听说的。
那些只不过是一些私下里的传闻而已,但他手中的文献现在却正以无比确实的口吻讲述着这失落之城的一切。
运河绕城,上有千万桥梁。河间以支线互通,帝后可以遍行城中。河运亦得入海,虽为内环者,三层之舟通行无碍。两岸高筑,桅高而能行于桥下。如不得高筑,则有活动开合之桥让行于舟。王宫所在之岛位于城中,正圆形,筑高塔御之,城门威严。所用之石,皆取自近岛或内外运河之地深处。高塔者,一白也,一红也,一黑也。城下采石所遗洞穴,皆以为藏身所,兵库,以及酒窖。是穴深,有石作顶,壁两层。建筑有清一色者,亦有杂色斑驳者。城墙之处最外环者,下临烟波,其石皆以铜加固,内侧所覆银也锡也。卫城要塞者,山铜也,光耀夺目者也。
柏拉图反复不断地默念着那奇异金属陌生的名字。(以下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