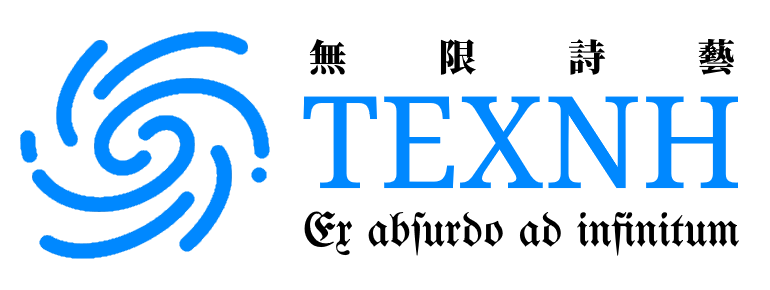美的产生
有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的产生是以有一个审美者为前提的,且需要一个审美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例如在博物馆里有一幅画,这画是举世无双的神作,是人人见了都赞不绝口的。但是,如果某一天博物馆不对任何人开放,即无人欣赏此画,且想见它别无他法,那么它就不再有其审美价值,因为根本无人能够审美。对此,这就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能为人所知的事实。其关键在于,审美的主体、执行者是人,而非审美对象。确定了这样一个关系后,我们就能讨论美感产生的因素了。
第一,关于审美对象。审美对象是审美的直接原因,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其质量直接影响了审美体验的质量。换言之,即是审美对象需要一些令人愉悦或是其他对人有价值的特点。例如一望无际蓝天白云遍地牛羊的草原风光,它就给人一种宁静豁达的感觉。这一过程是自然的,绝非人工干预。再如一个红色墙壁的房间,就给人紧张或炎热的体验。简单地说,审美对象需要自身有一种美感。当然,对象是否有美感则取决于人。一般,符合人的意愿的,特别是符合在生活中被压抑住的意愿的,对于特定的人而言是美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暴力美学”的存在。
第二,关于审美过程。这个因素相对比较客观,也较为偏向外部原因。一段诗歌,限定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求某人读完,恐怕这个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美。一篇美文,放在课堂上逐字解读马上可以令它味同嚼蜡。另外,也就不难想像一个好的环境,甚至是一个好的心情所造成的影响了。总之,对于审美过程的原则就是自愿,不论是什么原因,只要个人认为这样的审美合适,那就是有价值的,就可称为自愿。“暴力美学”在实践中的快感亦是这个道理。
第三,关于审美主体。审美主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是整个审美活动结果的最终接受者。一个具有高素养的审美者往往能更有效地审美。但审美主体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人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最终的审美效果远远多于审美对象所能提供的内容。最经典的例子便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一个没有动词表示逻辑关系的句子,为何能给我们如此丰富的联想,答案就在于意象的使用。人将某一事物与自己的经验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新的东西,在这里则是一种愁意。通俗地讲,就是“触景生情”。当然这个作用是相互的,人原本就有的情感可以被加在审美对象之上,这就是所谓的“移情于景”。正是由于审美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才有更多趣味。
虽然看上去以上三点仅是按次序一一排出,实际上它们皆有共同的原则,即符合人的意愿。通过审美,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中写道:“在他(马克思)看来,人们单纯地为了生产而自主进行的生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生产。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实现。但我们也可以在艺术这种特殊化的生产中提前体会到这种创造的滋味。”夸张地说,在神死之后,审美就是人对神位置的取代。
PS:第三点可以参考二次创作理论,这个忘记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