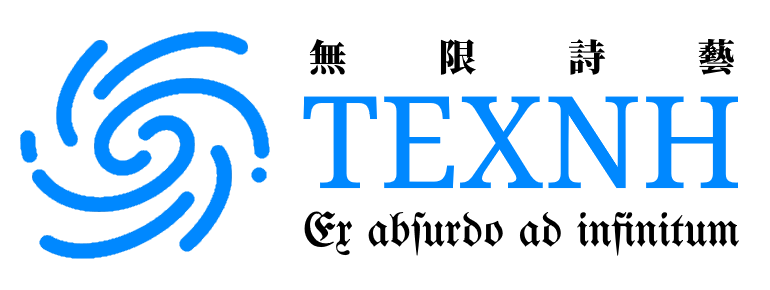Was war, was ist, was bleibt?
在这人为规定的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时间循环终结处,有必要再整理一些东西,毕竟不经整理的事物是难以留存下来的。
以此为契机,我们正好可以尝试一下用通常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来飙车,讨论一番何以留存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个所谓决定性的定性问题上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事物都不是以那种物理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说辞,“穷途末路”的现代科学与佛法的“不谋而合”在当下几乎要成为“陈词滥调”,但我也不怕劳烦地再试图吹吹牛皮。
我断言,我们头脑中使用的种种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存在,几乎都是取决于我们对其持有何种信念。历史上以及现实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想像的共同体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手指着某个它说:“看,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虽然也可以说它占据了一定的时空,但是要指出这种“占据”是无法在时空中找到标志性的依据的。或许有人会说它就是某个被规定了的时空中一切存在物的总和。我承认这一说法非常讨巧,但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有利于我的断言的因素,也就是“规定”,而“规定”又何尝不是一种信念?
我当然不是要说万事万物包括这种“想像的共同体”不存在,毕竟关于它们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很常用的,而且确实有用。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破除对于任意信念过分的执着。执着是必须的,所谓信念本身就有一定执着的意味,但过分的执着便是有害的了。信念本身只是一种人为的规定,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依据,但最终作成这种规定的必定是人,事物自身没有包含关于这种规定的任何暗示。这就意味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对任意对象作出任意规定。退一步说,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混沌的材料作出规定的可能性并不是唯一的。然而,此时如果有人持有某种过分执着的信念,就必然对其他可能性视而不见。事实上,人们对于同样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事物是如何可能的、如何被规定出来的意见也不相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增添了某种狂热,恐怕只能把人更深地逼进孤独的绝境。
但是这样一来,这种想法似乎就对我们讨论“留存”非常不利了。这种可以任意生成、消灭的信念对于探求如何使事物留存不仅毫无帮助,甚至使我们开始怀疑事物究竟是否能够留存。也许“留存”本身就是一种过分执着的信念?如果是,那我们又应当如何对待它?关于这一点,我尚不能完全说清,这自然意味着我可能还没弄明白,因此只能留待下次讨论了。